汽车零部件行业入局航空制造业的思考
现在有非常多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入局航空制造业,昨天去了一家汽车行业全球百强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他们正在准备进入航空业,在沟通中间简单讨论了一下管理模式的差别,结合前些天在一个汽车零部件行业看到飞行汽车对他们供应商管理模式。昨晚在回上海的高铁上,我就在继续想这个问题,现在用汽车行业这套模式运用到航空制造业上面去会有什么影响。

我先说一下我的印象,总体上来说我感觉是非常负面的,虽然汽车行业有很多管理模式,如AS9145航空业APQP也在学习汽车行业的六大工具,AS13100航空发动机体系中吸收了大量的汽车行业成熟管理经理,如VDA6.3过程审核之类的。这种负面印象主要不是管理技术上的,主要是管理理念上的。
说到这我就先描述一下这二个行业之间的差异,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大领域,传统大飞机制造业,低空飞行器制造业,以及汽车制造业,现在很多汽车制造业是入局低空飞行器制造业。这是介于传统大飞机和汽车制造业中间的一个领域。
首先是业务运营模式的差别,说一千道一万,企业是要赚钱的,赚钱的模式就决定了其它所有方面的差别。
汽车业务:多以批量生产零部件、按订单销售为主,盈利集中于产品出厂环节,后续服务(如维修、替换)占比低且周期短(汽车零部件更换周期多为 3-10年特别是现在新能源车更短)。
航空零部件的使用周期长达 10-30 年(如飞机发动机、结构件),且维修、维护、升级需求贯穿全生命周期。企业可围绕 “产品 + 服务” 设计盈利链条:
前期销售核心零部件(如客舱内饰、电子系统组件);
中期提供定期检测、故障维修、备件替换服务(按服务次数或时间收费);
后期参与老旧部件升级改造(如将传统座椅升级为轻量化智能座椅),获取持续服务收益。
如霍尼韦尔航空业务中,维修服务收入占比超 40%,远超单纯零部件销售利润。
从 “短期订单盈利” 转向 “长期协议 + 风险共担盈利”
传统汽车业务:订单周期短(多为 1-3 年),盈利与车企年度产量强绑定,价格谈判中议价权较弱(车企常通过压价降低成本)。
航空业差异化模式:
航空项目周期长(如大飞机研发需 10 年以上),客户更重视供应链稳定性,企业可通过 “长期协议 + 风险共担” 锁定利润:
与主机厂签订 5-10 年的长期供应协议,约定基础采购量 + 价格调整机制(如按原材料涨幅同步调价),保障稳定现金流;
参与航空型号的早期研发(如在 C919 研制阶段介入内饰设计),以 “研发投入换长期订单”,并在量产后享受优先配套权(通常可获得 30% 以上的独家供应份额);
上周我问一个汽车零部件入局航空企业,报价时有没按汽车价格的20倍报,企业的业务部门一脸蒙圈,不知道还可以这么报价。
将传统汽车行业 “严格控制供应商报价、追求低成本” 的模式直接套用到传统航空以及低空飞行器领域,本质上是对 “安全优先级” 的挑战 —— “空中安全冗余” 的核心需求与 “低成本导向” 存在天然冲突,低成本逻辑与空中风险的不可调和。

传统汽车的 “低成本控制” 有其合理性:地面环境相对可控,即使零部件存在微小瑕疵(如塑料件强度略低、电子传感器响应延迟 10ms),也可通过整车安全设计(如车身结构、冗余系统)或使用场景限制(如城市道路限速)降低风险,且行业允许 “可接受的故障概率”(如 ppm 级失效)。
但 “空中安全” 容不得半点妥协:
• 单点失效可能致命:例如,降低成本选用普通汽车级电机而非航空级冗余电机,一旦空中停机且无备份动力,直接导致坠落;若为压价缩减电池测试环节(如省略极端温度循环测试),高空低温环境下电池突然断电的风险将陡增。
• 连锁反应波及公共安全:飞行汽车在城市低空飞行时,任何零部件故障(如螺旋桨连接件断裂)不仅危及乘员,还可能砸向地面人群或建筑,其安全责任远超个体,属于 “公共安全高敏感领域”。
当企业强硬要求供应商 “降价 10%”“替换低成本材料” 时,供应商可能被迫简化工艺(如减少无损检测步骤)、降低材料等级(如用汽车铝合金替代航空级铝材),这种 “成本挤压” 实质是在 “安全冗余” 上让步。
传统汽车供应链的 “低成本能力” 建立在标准化、规模化基础上:例如,同一型号的汽车螺栓可年产百万件,通过集中采购、通用模具压低成本,且性能只需满足地面工况(如常温、低振动)。

但航空部件采购量相对汽车业,是非常非常小,单品价格低情况下,让供应商如何生存?
供应商若妥协,产品将沦为 “伪航空级”;若拒绝,可能被替换,这种 “低成本绑架” 会引发供应链对 “技术底线失守” 的担忧,进而导致优质航空供应商不愿合作,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 的恶性循环。
真正适配航空制造的供应链逻辑,应是 “安全底线不可破” 前提下的成本优化:例如,通过技术创新(如新型复合材料)降低安全冗余的边际成本,而非牺牲安全本身。唯有如此,才能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还有是质量和产品安全管理理念的差别
安全逻辑的冲突:从 “地面容错” 到 “空中零容忍” 的落差
传统汽车的安全模式建立在 “地面环境相对可控” 和 “事故后果有限” 的基础上:例如,汽车刹车失灵可能通过路边摩擦、碰撞缓冲带等方式降低风险,即使发生故障,也有 “被动安全”(如气囊、车身吸能)兜底,行业对 “极低概率风险” 的容忍度较高(如百万分之一的失效概率)。
 如飞行汽车作为 “低空航空器”,安全逻辑是 “空中环境零容错”:
如飞行汽车作为 “低空航空器”,安全逻辑是 “空中环境零容错”:
•空中没有 “缓冲带”,任何动力系统、控制系统的故障都可能直接导致坠落,后果是 “全损性灾难”;
•其安全不仅涉及自身,还关联地面人群、建筑(如城市低空飞行时,故障可能砸向居民区),属于 “公共安全高敏感领域”。
当车企沿用 “汽车级安全标准”(如仅满足 ISO 26262 功能安全)来设计飞行汽车时,会让用户和监管方产生强烈的 “安全焦虑”—— 例如,某车企将汽车的电池热管理系统直接移植到飞行汽车,却忽视高空低温、低气压对电池性能的极端影响,这种 “经验主义” 会引发对其安全专业性的质疑。
场景适配的错位:从 “封闭道路” 到 “立体空域” 的能力断层
传统汽车的运营场景是 “二维封闭道路”:有明确的车道线、交通信号灯、地面标识,依赖 “人 - 车 - 路” 协同(如导航地图、交通监控),车企只需聚焦 “车辆本身的驾驶性能”。
而飞行汽车的场景是 “三维开放空域”:
•需应对复杂气象(侧风、暴雨、低空乱流),这是汽车从未遇到的环境变量;
•空域权属于国家管制资源,飞行路线需提前报备,且可能与无人机、直升机等共享空域,涉及 “空管协同”“避障优先级” 等全新规则;
•起降场景多元(屋顶停机坪、城市 vertiport、应急场地),对垂直起降效率、场地适应性的要求远高于汽车的 “平面停放”。
若车企仍用 “造车思维” 定义飞行汽车(如宣传 “像开车一样简单”,却未解决空域申请、气象预警、多机协同避障等问题),会让用户觉得 “产品离实际使用太远”—— 例如,某车企推出的飞行汽车原型机续航达标,但因未接入空管系统,实际只能在指定测试场飞行,被质疑 “沦为玩具”。
员工认知差异
汽车行业:质量要求更多体现为 “职业规范”,员工遵循 SOP(标准作业程序)即可,对 “质量背后的生命价值” 关联感较弱(如 “我生产的座椅卡扣只要通过强度测试就行”)。
航空行业:质量意识已升华为 “行业信仰”,员工对产品的安全性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
汽车制造业入局航空零部件,表面是技术与标准的升级,实则是质量文化的 “基因重组”—— 需要将 “效率优先” 的底层逻辑替换为 “安全冗余优先”,将 “合规底线” 提升为 “信仰级坚守”。这种转变无法通过简单的制度移植完成,必须从员工认知、流程设计、组织评价等维度进行系统性重塑,最终实现 “每个动作都带着对生命的敬畏” 的文化自觉。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跨越隐性质量文化的鸿沟,在航空领域立足。
我越来越感觉到,有些潜在的文件是不通过学标准看文件就可以解决的,一定要在这环境下工作过,体会过,才能感知到,例如国外航空企业找国内数控加工企业,一般是一定要做过航空件的企业,我们这数控加工企业多如牛毛,他们为什么不选没有航空制造经验的,有些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二个行业我都去过很多,我有个印象是汽车行业造假记录是大大多于航空业,航空业记录造假基本上没有,这个行业特点决定不太可能这样运行质量体系。
有个行业和航空制造业是非常象的,就是医疗器械,如果你同时学了AS9100和ISO13485就会有这样感觉,这二个怎么这么象,
航空质量体系(如 AS9100)和医疗器械质量体系(如 ISO 13485)均服务于高风险、高可靠性要求的行业,二个都是合规性与法规导向,医疗器械关注患者安全,需评估产品对人体的潜在危害(如感染风险、功能失效)。我见过很多航空制造业同时做医疗器械行业,非常有名的就是无锡航亚,同时做航发和医疗器械产品,二个管理理念的融合度是非常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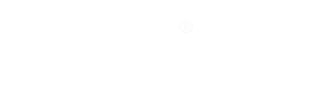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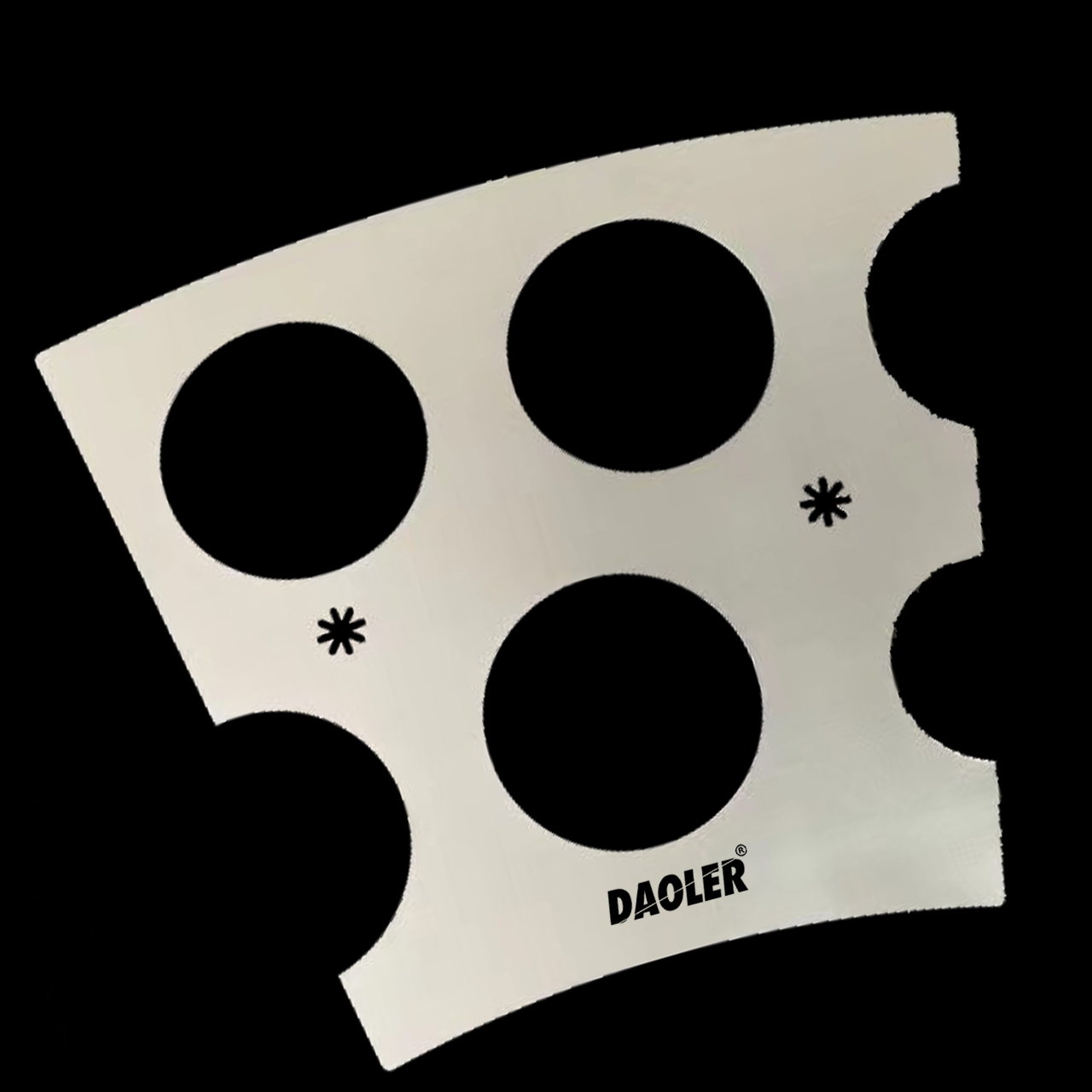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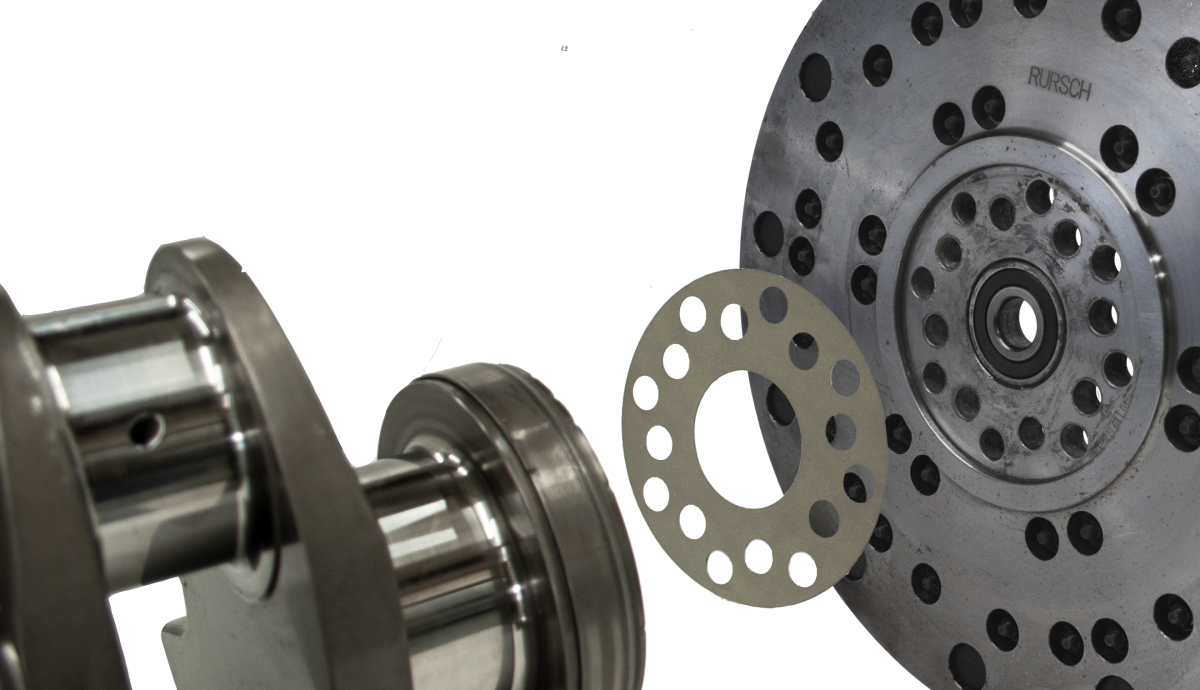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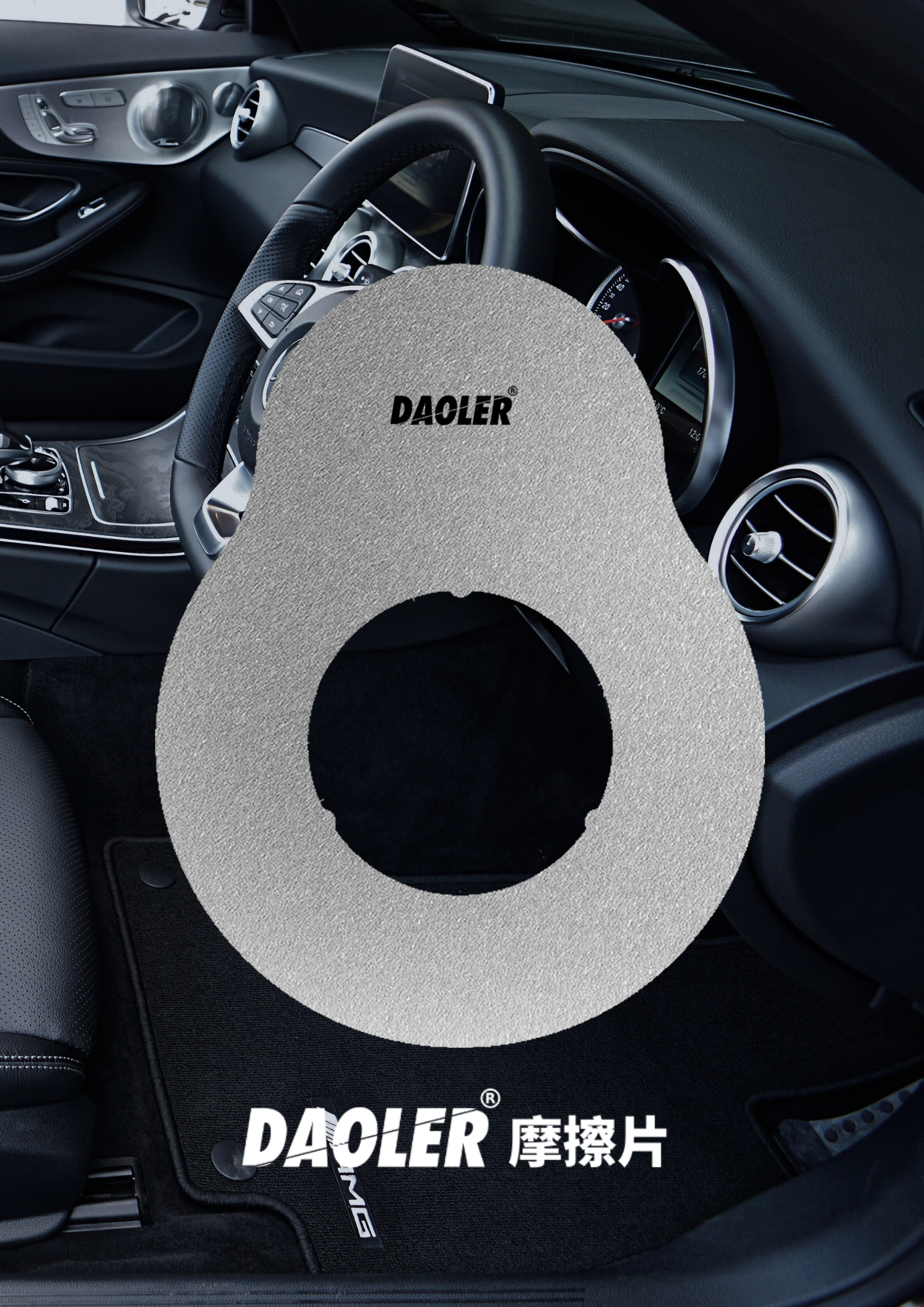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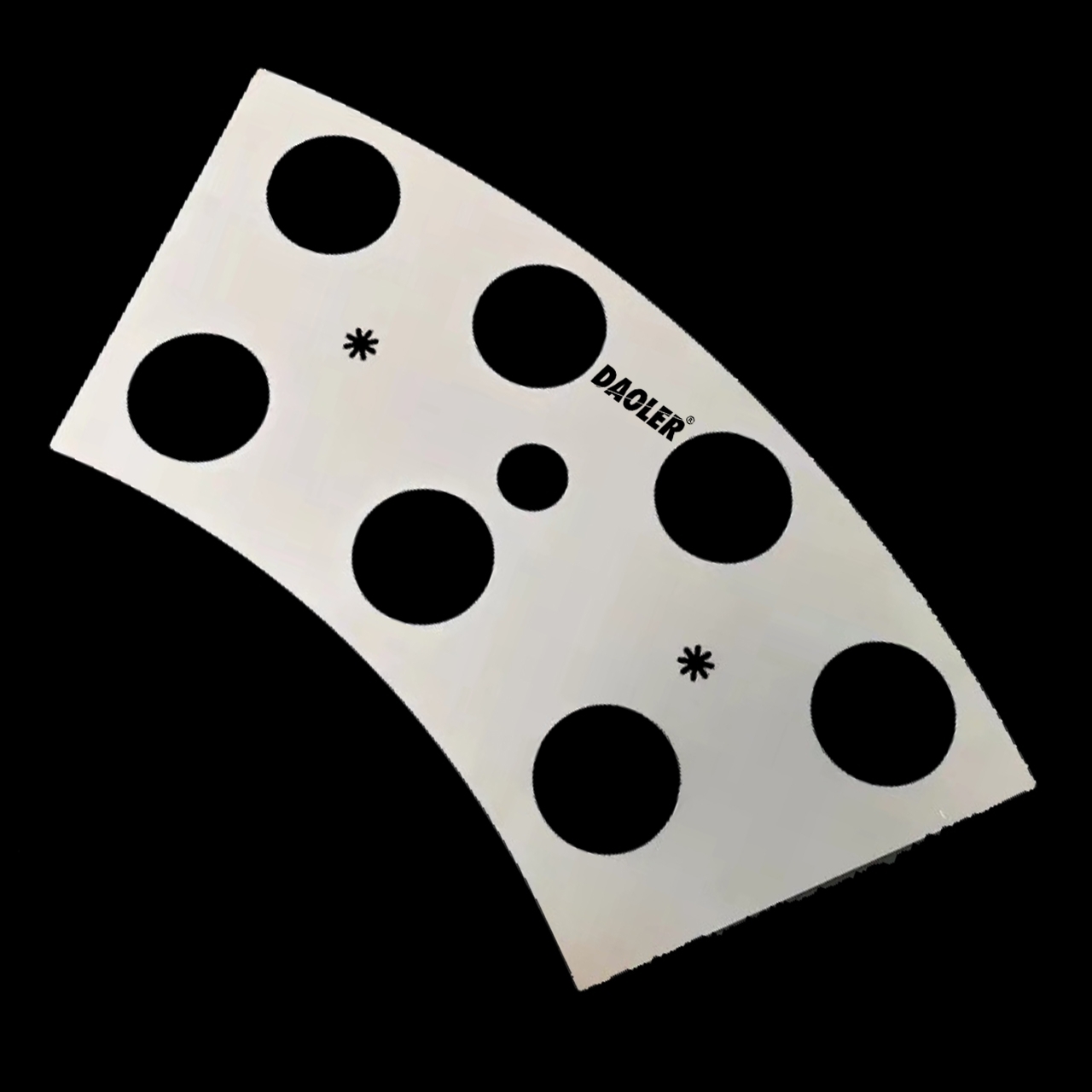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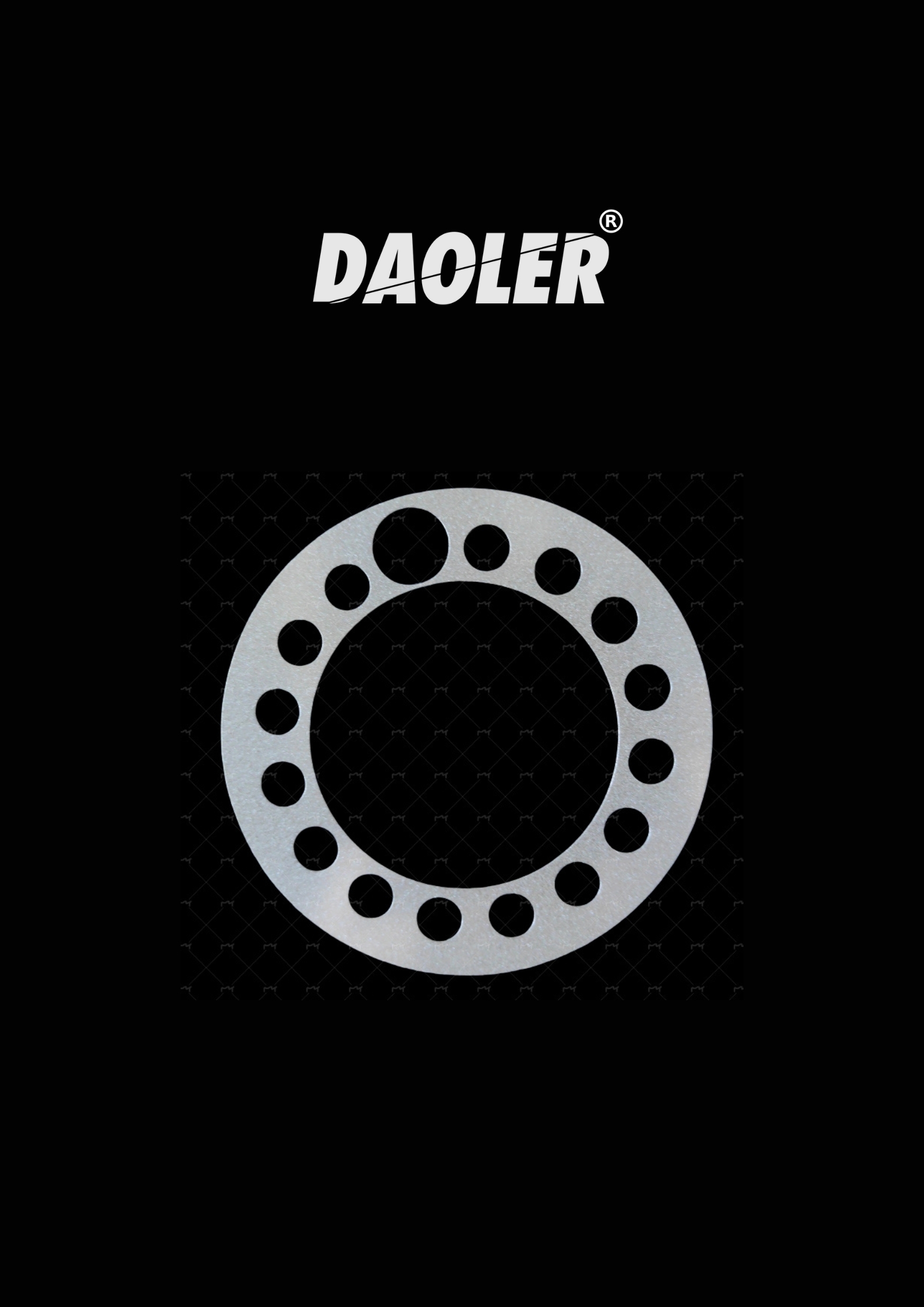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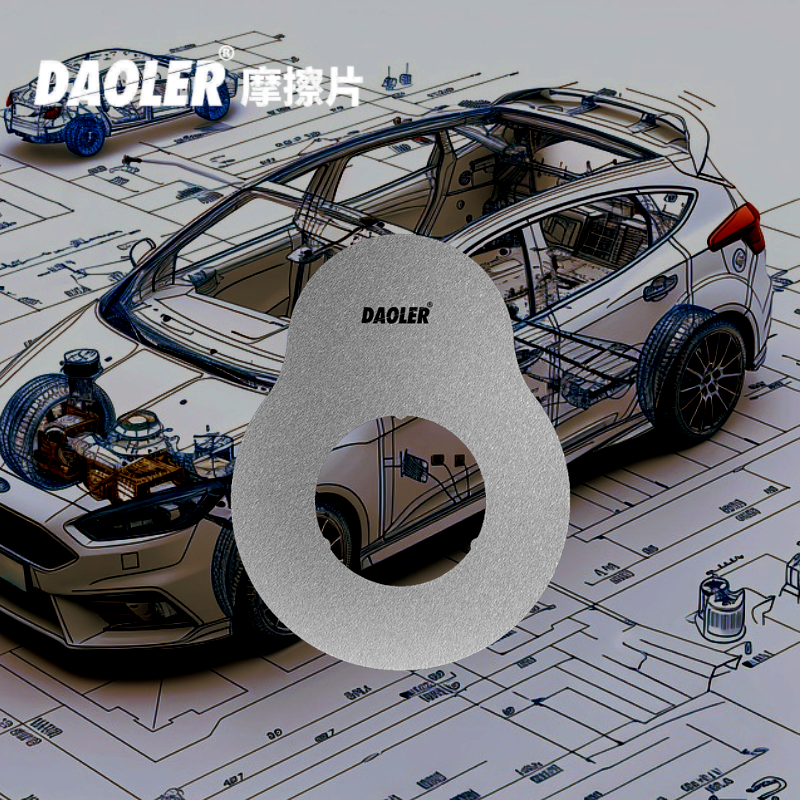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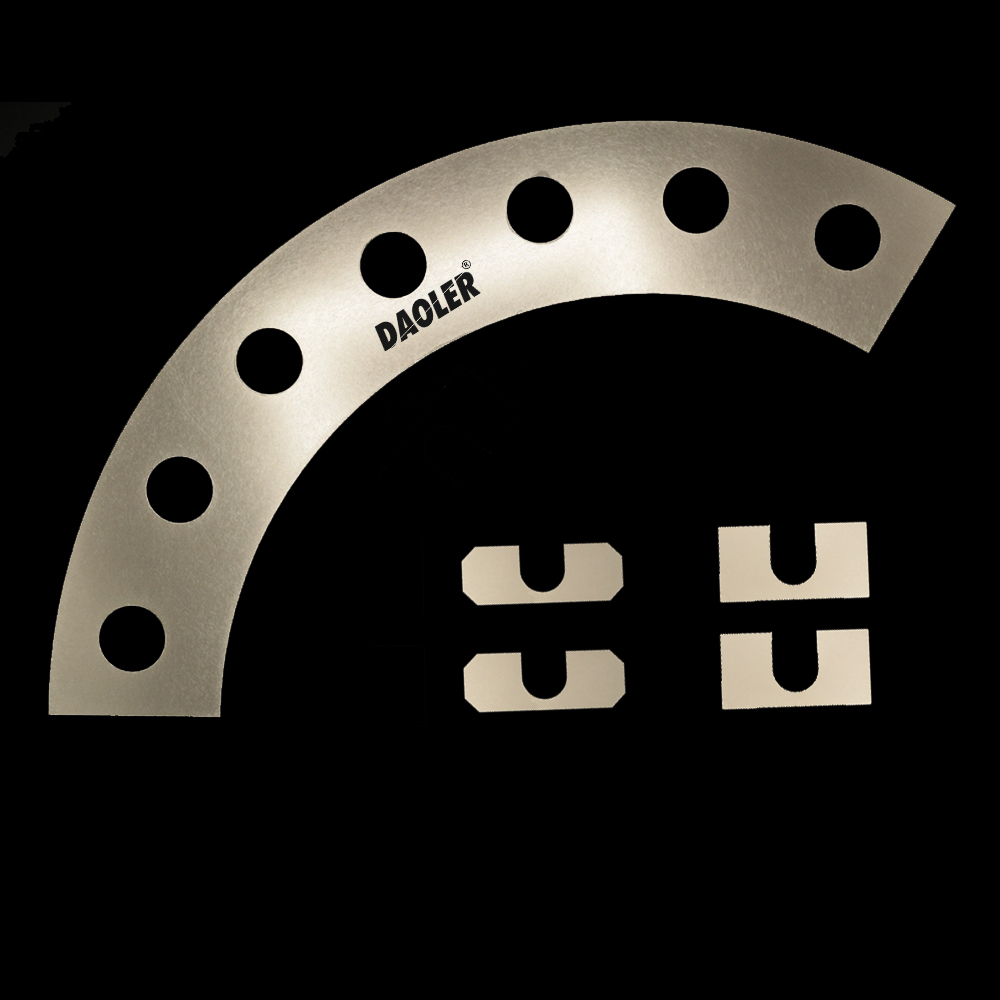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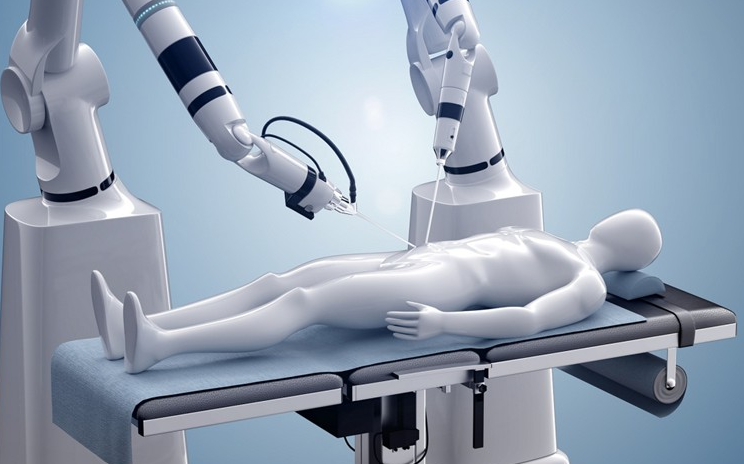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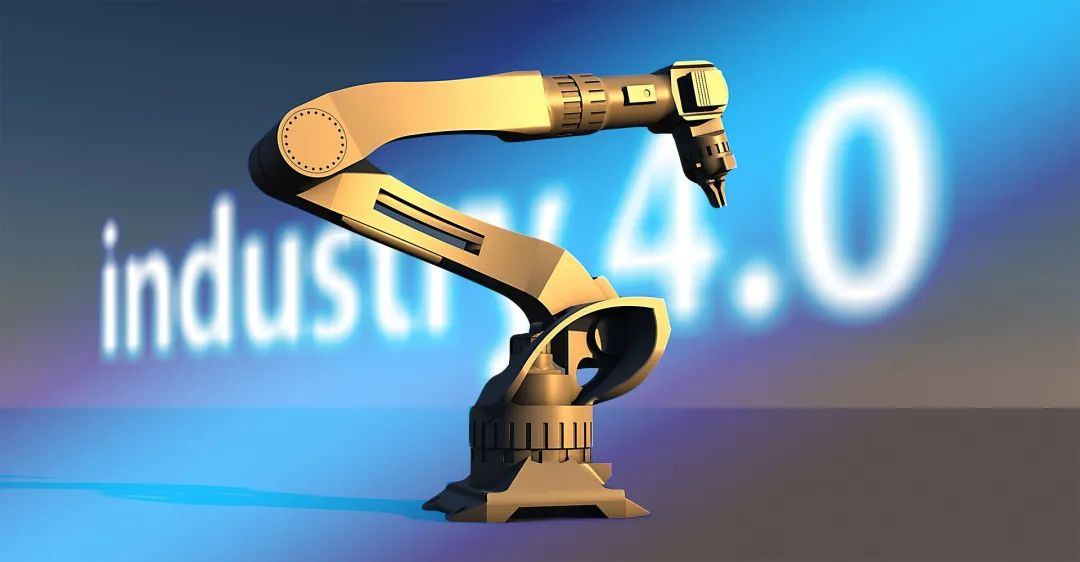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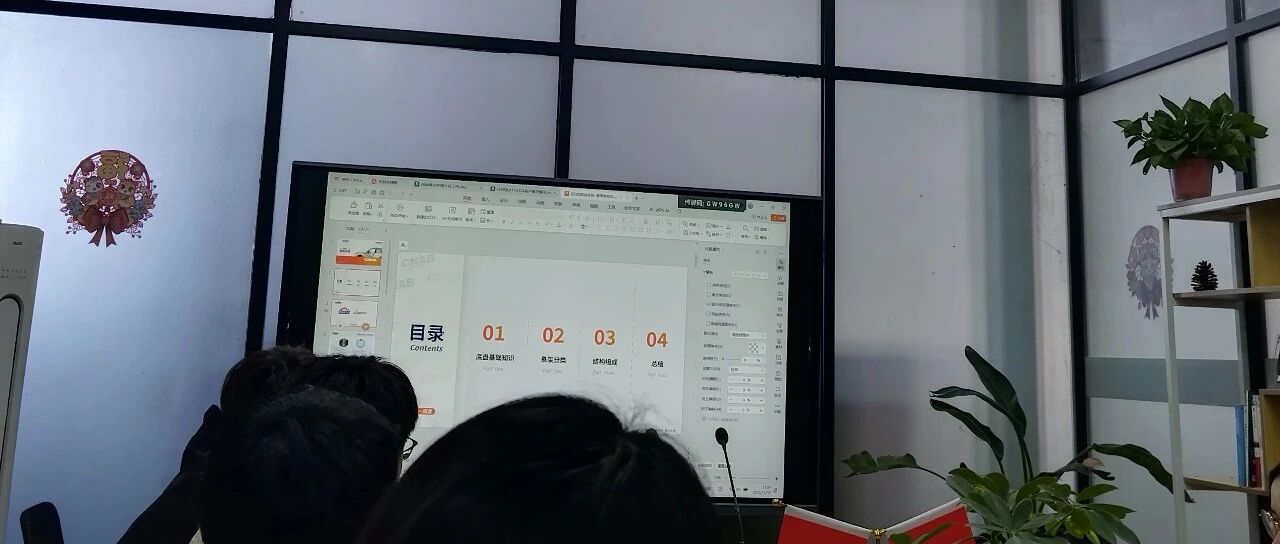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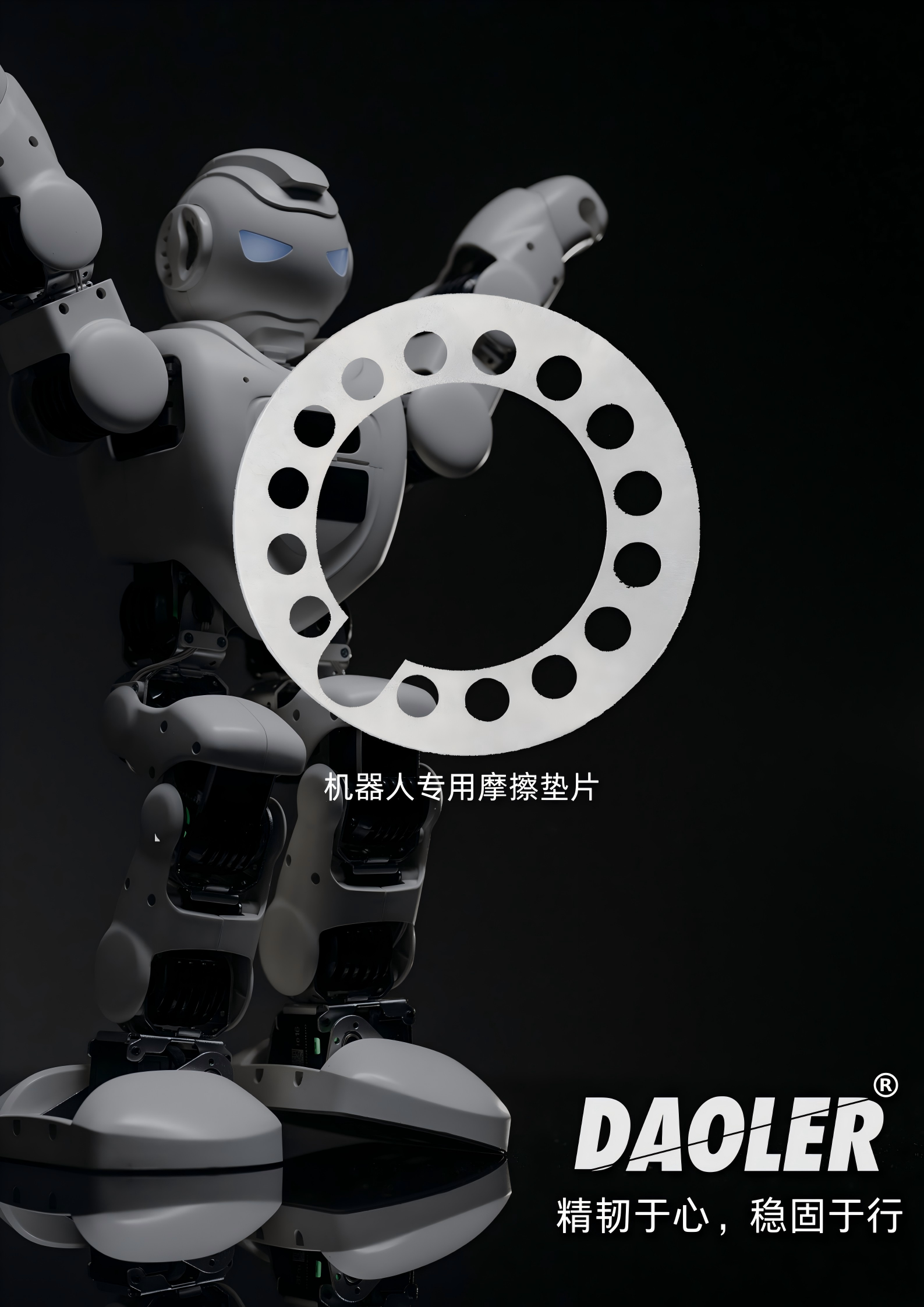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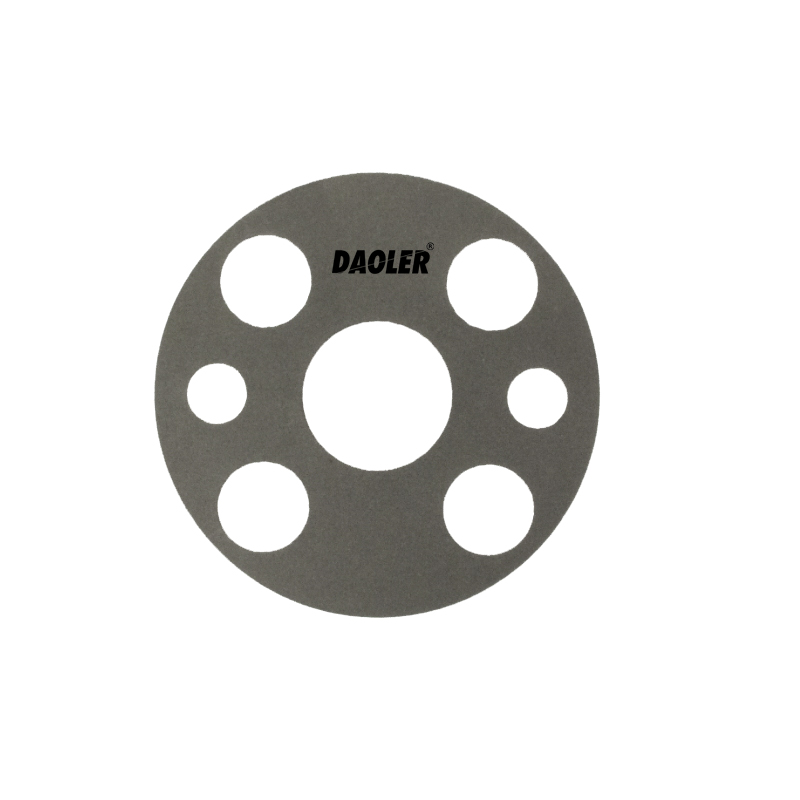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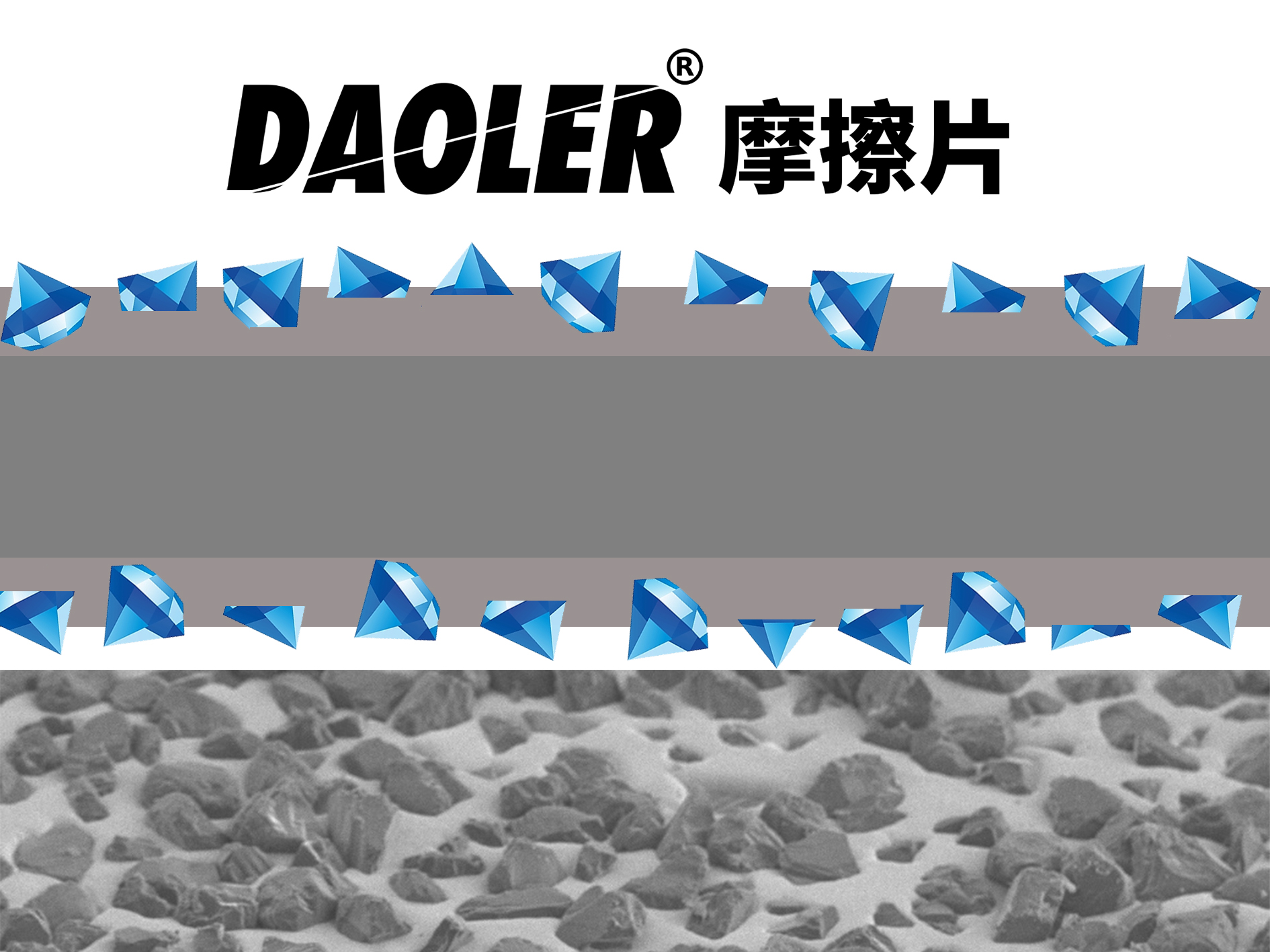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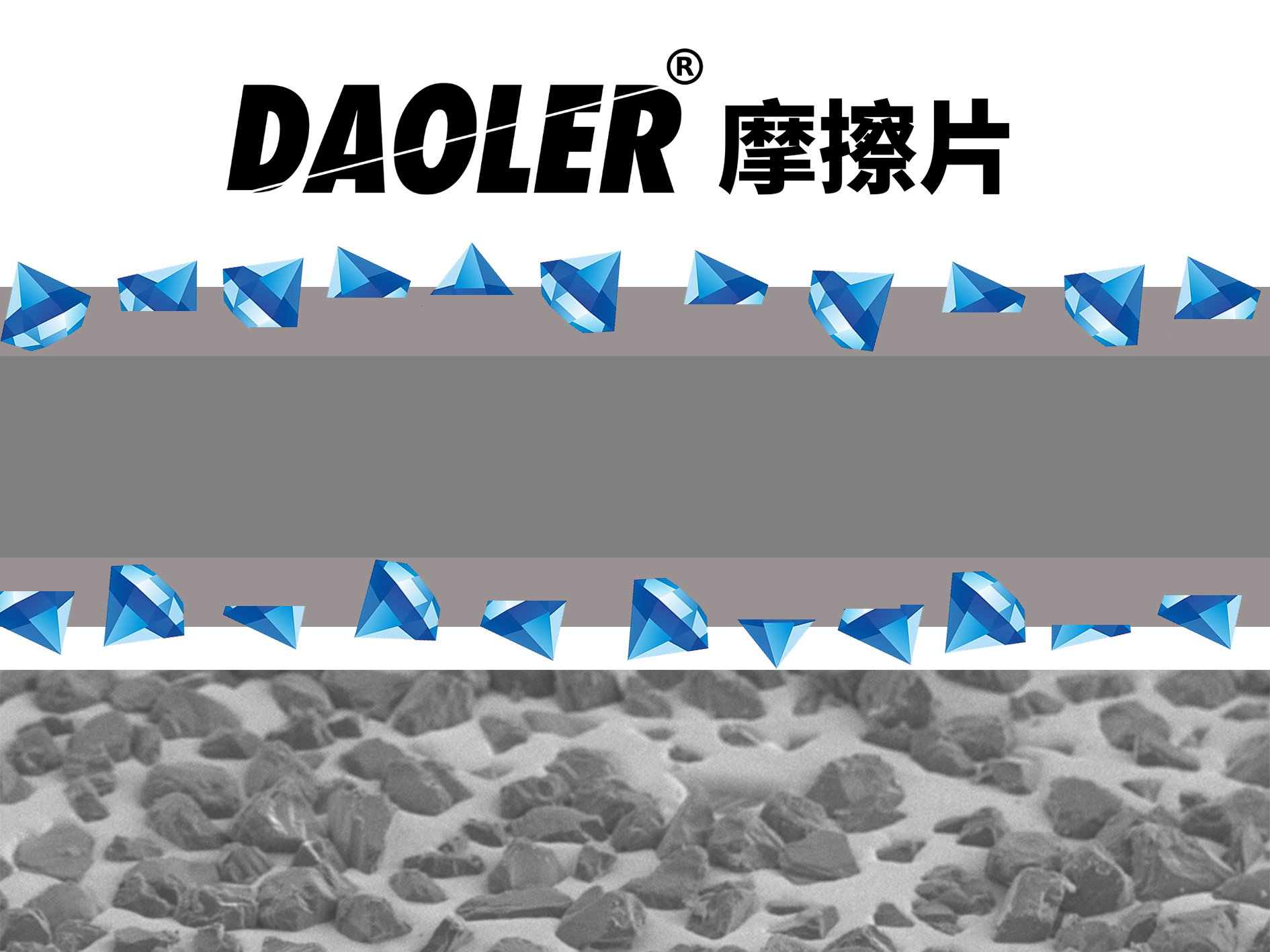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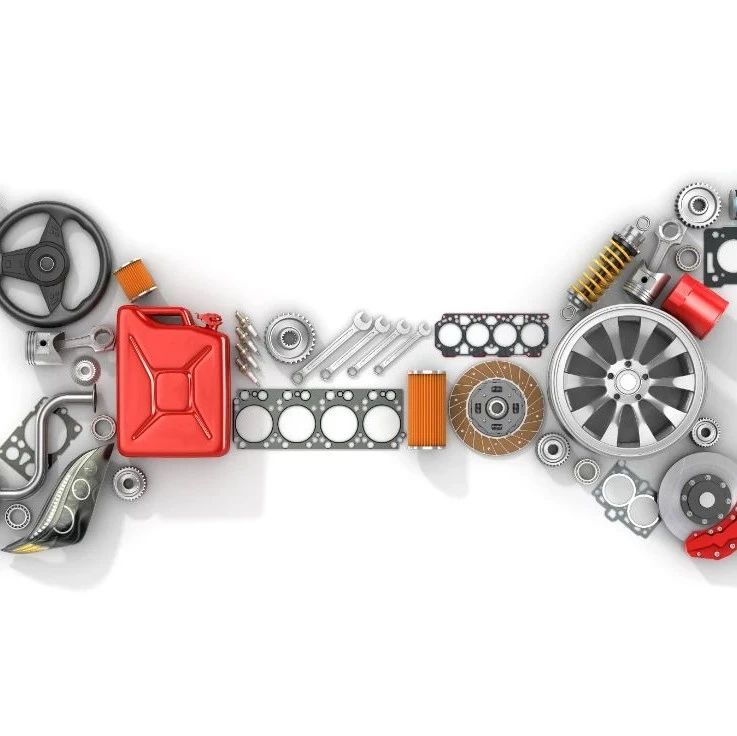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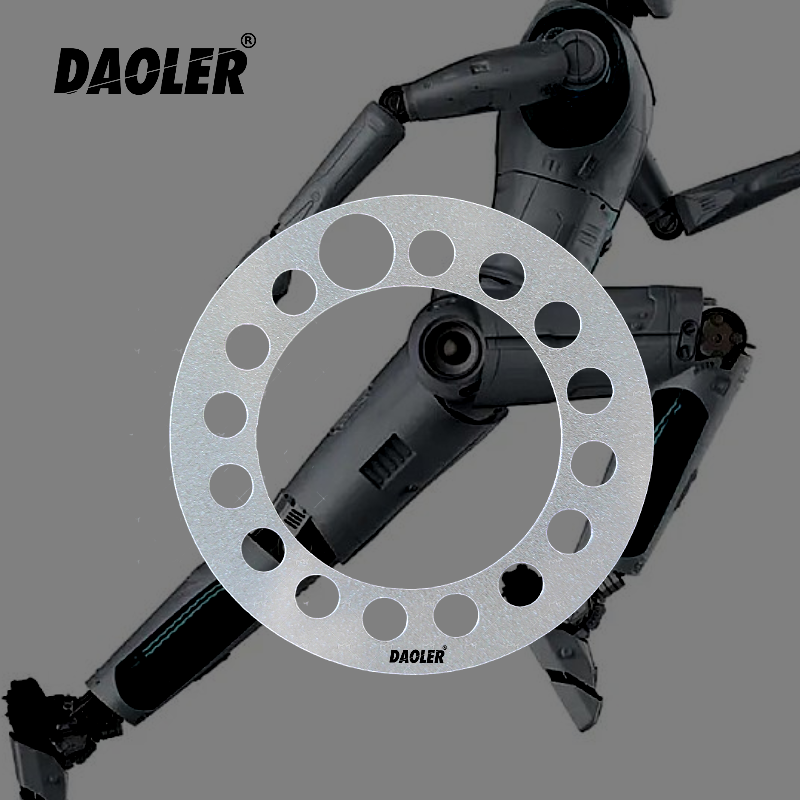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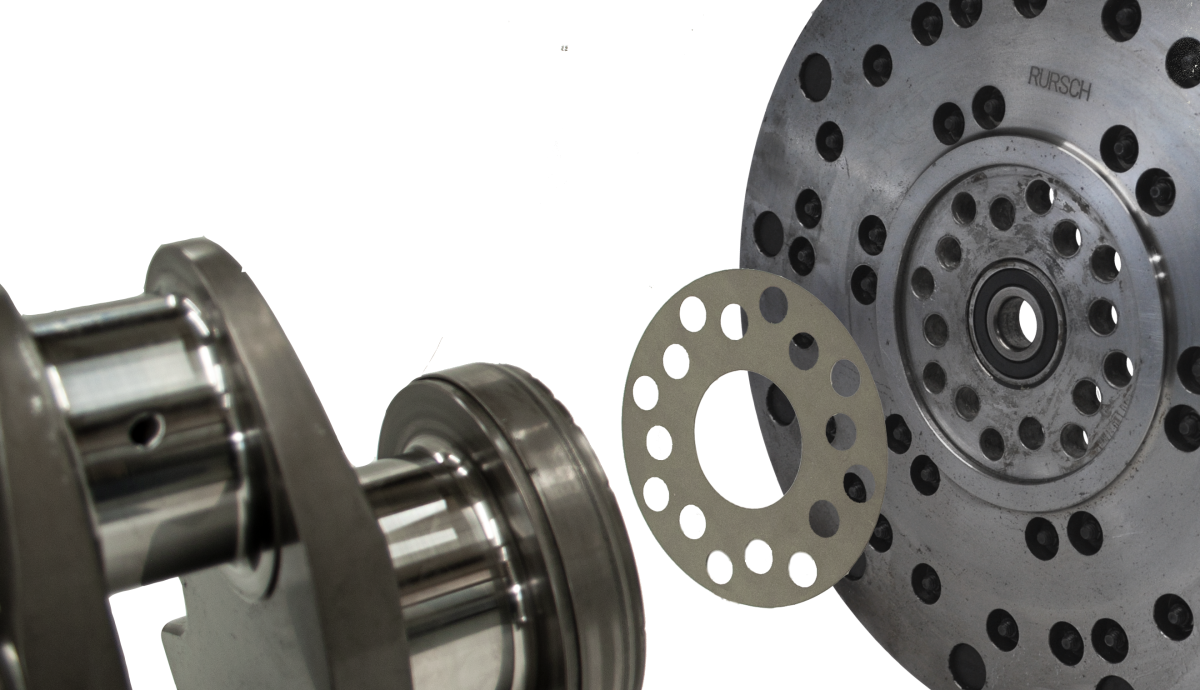



请先 登录后发表评论 ~